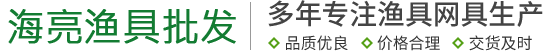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际,英国出动了兵力达1.4万余人的3个旅,还派遣了包含航空母舰在内的21艘军舰,以及80多架飞机,参与到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之中,英国由此成为除美国之外出兵数量最多的西方国家。
英国的这种军事参与,更多的是为了维持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展现出的一种政治姿态,这实际上也将曾经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在战后国际格局里的尴尬境地暴露了出来。
当时担任首相的艾德礼尽管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持有不同看法,可是在杜鲁门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只能做出妥协。然而,他们也十分明白,新中国手里掌握着他们很大的把柄。
香港处在南海之畔,它和中国大陆仅被一条深圳河分隔开来。香港于英国而言,是其在远东地区的“皇冠明珠”,堪称帝国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不过香港的经济命脉与大陆有着紧密的关联,因而可以这样讲:“香港是否安定,新中国政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之际,以四野的作战能力而言,只要华南局下达命令,数小时之内就能够将驻香港的英军彻底击溃,不过解放军却未采取行动。
在毛主席等领导人深谋远虑的考量下,当时不收回香港,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遭受西方封锁时,需要留存一个与西方进行交流对话的通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英国有所顾虑,不至于完全依照美国的想法与中国敌对。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港英殖民政府的官僚们在以当时的港督葛量洪为首者的带领下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在其贸易总量中所占比例达到37%,内地供应的粮食、日用品满足了香港民生需求的60%以上。
由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全面禁运政策,事实上让香港陷入了两难之境:要是严格遵循禁运规定,香港的转口港地位将会丧失;要是表面遵从实际违背,就有遭受美国制裁的风险。
1951年5月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决议之后,这种矛盾趋于极致,港英政府只得颁布《进出口(战略物品)规例》,不过暗中却保留了“例外许可”制度。
港英政府的官员那时心里很明白:“我们必须在华盛顿的强大压力和香港的实际状况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档案资料表明,在1951到1953年期间,香港向中国大陆输出的“非战略物资”,其出口额逆着当时的形势增长了23%。
纺织品、药品、钢材、汽油、煤油、柴油以及五金、麻包等“灰色物资”,经由复杂的报关手续不断地向北运输。
更为过分的是,港英政府的海事处居然对有关系的特定商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为其签发了“特别通行证”。这些商船在夜间出港之后便关闭应答器,顺着大屿山西侧的隐秘航道朝着澳门驶去。
与香港面临诸多限制相比,处于葡萄牙治理之下的澳门由于其中立的地位,成为打破禁运的重要节点。澳葡政府很机智地运用《中葡友好通商条约》留存的条款,把贸易管制的标准确定为“非军事用途物资”。
这种政策的不明确性催生了一种独特的贸易生态:1951年澳门注册的贸易公司数量相较于1951年大幅增加,像南光公司、南华公司之类的中资机构凭借隐蔽的管控布局,搭建起了一个遍及东南亚的采购网络。
南光集团的运营可谓是隐蔽战线的楷模。其位于澳门的总部位于殷皇子大马路一座毫不起眼的骑楼之中,借助何贤、马万祺等爱国商人的社会关系,构建起三套彼此独立运行的体系:
采购团队打着“南洋贸易行”的名号与供应商接洽,运输团队凭借“广昌船务”调配船只,结算团队借助澳门银号开展离岸资金的清算工作。
为逃避检查,重要物资常常运用“二次包装”的手段。像五金器材会被标记为“农具配件”,抗生素则被乔装成“鱼肝油制剂”,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
在这场贸易角逐里,的创业历程可谓是时代的一个写照。霍氏家族源于疍户,他们在海上遭遇诸多劫难。1923年,一场台风致使的两位兄长丧生;到了1930年,的父亲因病离世,那时全家仅剩下几件破旧的渔具。
的母亲刘氏携三个孩子上岸之后,于湾仔坚尼地道搭棚居住,靠着给人缝补衣物维持生计。不过常言说得好,患难之中出英才。年纪尚小的在皇仁书院半工半读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商业方面的天分了:他把校园汽水销售的业务承包下来,凭借“买十送一”的方式每日能售出百瓶。
抗战胜利之后,凭借母亲典当首饰所换得的数百港币起步,购买了一艘全无动力装置的小帆船来开展海上运输业务。朝鲜战争爆发之际,27岁的刚刚组建起“信德船务”。
由于他对海况十分熟悉,所以最先察觉到澳门的贸易机会:在新加坡购买橡胶,经马六甲海峡运至香港,再改装到渔船上于夜间航行至澳门,每次航行的利润能够达到300%。
之后,的运输业务拓展到柴油方面。由于柴油的密度比水小,承载柴油的船只吃水较浅,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旁人看不出船上装载的物品是什么,这在局势不太稳定的东南沿海区域是比较安全的。
霍氏船队为了应对海上风险,开创性地设立了“三船联保”机制:领航船装配望远镜用以侦察,运输船加装加固钢板,护航船则部署武装人员。
起初,并不知晓,在他负责运输的橡胶、柴油等物资的背后,其主要买家是由我党华南局直接管控的“南光公司”。
运送那些“禁运”物资相当频繁,并且他给出的价格合理,货物总是能按时送达。正因为如此,南光公司的负责人开始关注他,并且对他十分重视,还把他当作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之一。
当然,运送这些紧俏物资的航线绝不是一路顺遂的。的船只所运货物的种类较为特殊,这就吸引了特务的目光。他们与港英政府相互勾结,炸沉了霍家的一艘货船来进行警告。
还有一回,又有一艘货船被殖民政府的水警船撞沉了,遭受的损失相当巨大。不过在那个时候,心里已经清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也明白自己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但他依旧坚定果决地坚持了下去。
霍氏船队在港英当局与特务的干扰破坏之下,把传统帆船改造成混合动力的形式,以风帆作伪装保留下来,实际上是凭借改装过的美制GMC发动机来提供动力的。
货舱的设计极具智慧:通过向双层底舱注水来调节吃水的深度,在夹层里填充软木以确保在意外沉没时能够产生浮力。
最为巧妙的当属移动货仓系统,船员把货物分别装在可拆卸的铁箱里,在遇到检查的时候,这些铁箱能够迅速沉入预先设定好的海底坐标处,等到风险消除之后再进行打捞。
霍氏船队的运输效率因这种技术创新而提高了三倍。在1952年的高峰时期,该船队每月能完成20航次,其运输量在澳门转口贸易中所占比例达到了15%。
南光公司的档案资料显示,于1951年至1953年期间,总共运输橡胶达5000吨、钢材达1.2万吨、药品400多箱。这些物资在天津港卸货之后,通过铁路悄悄转运到丹东前线。
诚然,与白道的人打交道还比较容易应付,可黑道之人行事毫无顾忌,这就更为棘手了,稍有不慎,自身以及船只都会陷入危险境地。
在珠江口,从香港至澳门有着大概60海里的水路。这一被殖民者强行分裂的水域当中,当时正有三方势力在其中活动:挂着米字旗的港英巡逻艇、带有青天白日徽标的炮舰,还有那些被叫做“大天二”的亡命之徒。
那些由溃败士兵、海盗以及黑帮成员拼凑而成的武装团伙,就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群一样,在航道上疯狂地掠夺。
他们配备着美国援助的M2重机枪以及日本制造的鱼雷艇,就连港英的水警见到他们都得避让,澳葡当局对此则是有怒不敢言。
1950年冬季的一天,亲自押送一艘装有钢管的货船由香港驶向澳门,然而行至半途,却被一群来路不明的武装人员阻拦。
对方的装备十分精良,快艇的航行速度更是远远超过货船。要是把他们惹恼了,不但货物保不住,就连自身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心里很清楚,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海盗把整船的钢管抢夺而去。
之后,凭借自身的人脉关系了解到,抢劫货船的正是“大天二”。他不愿就此忍气吞声,于是决定亲自前往澳门,企图搜集证据,从而向殖民当局起诉对方。
他抵达澳门后便展开暗访与明察,没过多久还真看到有一群人正在码头售卖钢管,无巧不成书,那正是之前自己被抢夺的那一船货物。
当时的年仅27岁,正值年轻气盛、无所畏惧的年龄,他当即前往去讲道理,并且宣称要到澳门警署去控告这群人。
没料到对方竟然无动于衷,不但没有显露出一丝害怕的模样,反倒叫卖得越发起劲儿了。极为恼怒,刚要走上前去动手,却没料到后脑勺突然传来勃朗宁手枪那独特的击锤声。
猛地一愣,察觉到枪管正缓缓沿着脊椎朝着脖颈滑动,身后之人冷笑一声说道:“要是还这么吵闹不休,我就一枪崩了你。”
彼时的香港、澳门,社团林立,帮派纷杂,街头血拼仇杀就如同日常之事,当街被枪击身亡者屡见不鲜。明白自己此刻性命攸关,只能忍辱负重悄然从人群中退出。
返回酒店后,他反复思量,始终觉得这口气难以咽下,于是前往澳门警署去报案。可没想到的是,澳门的警察更加惧怕的“大天二”,只是敷衍了事,这件事最后根本没有任何结果。
多年之后,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印象深刻。他说道:“没料到搞海上运输险些吃到大天二的子弹。”
然而,这般惊险的经历却进一步稳固了拥护新中国的信念。毕竟,他不但听闻,而且亲见在新中国不存在海盗,没有土匪,看不到趾高气扬的外国警察,也没有诸如“黄赌毒”之类丑恶的事物。
在其一生里,从未接受过港英政府或者英国政府授予的任何荣誉勋章,不过,他很乐意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这一职位,参与到香港回归筹备的各项工作之中。